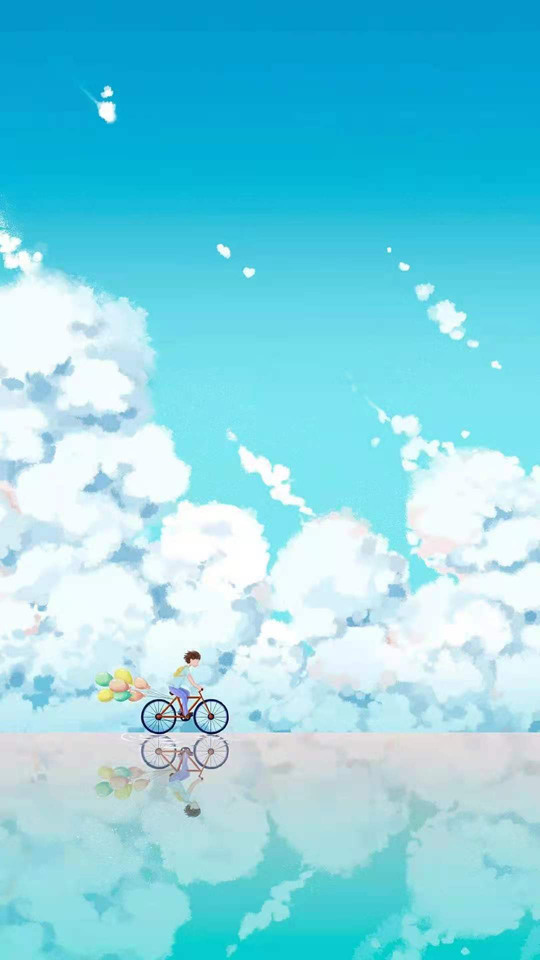我1955年6月出生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那时我父亲郑洪升是解放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的哲学教员。我父亲只上过三年私塾,他如果要将当教员的职业持续下去,需要刻苦自学。从我出生起,见到最多的场面,是父亲趴在桌子上看书写字,父亲是抱着一岁的儿子郑渊洁看完《资本论》的。我家收藏至今的那本《资本论》第955页右侧空白处的铅笔道儿,就是我的“眉批”。由此,我从小就对看书和写字产生了崇拜心理。
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如果我“犯了事”,父亲“惩罚”我的方式永远是写检查。我读到小学四年级时,遭遇“文革”,自此中断学业,跟随父亲到河南农村五七干校。在干校子弟学校,我因为将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早起的鸟有虫子吃》改写为《早起的虫子被鸟吃》,被老师开除。我在家写好检查等待父亲从农田回来,他一进家门,脸色很不好看,明显是获悉了我被开除的信息。
我将检查呈上——那篇检查我下了工夫,写成了小说。父亲看着看着,脸上就阴转晴了。我离开学校后,父亲在家教我,他给我上的第一节课,是让我背《共产党宣言》,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自己查字典。
我成为父亲后,继承了父亲家教的衣钵。对于孩子,只做不说。换句话说:闭上嘴,抬起腿,走自己的人生路,演示给孩子看。作为父亲,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是身教。儿子郑亚旗两岁时,我开始一个人写《童话大王》月刊。我之所以能一个人坚持写一本月刊几十年,很大程度是为了演示给儿子看:父亲靠一支笔,让家庭丰衣足食。我以为,父亲的身教,比要求孩子考一百分管用。
郑亚旗从18岁生日那天起,我没再给过他一分钱。他先是到一家新成立的报社,靠筹建和维护网站以及维修电脑挣工资养活自己。三年后,已经是该报社技术部主任的他辞职,创办《皮皮鲁》杂志,运作我参加各种电视节目,筹办由我主持的脱口秀《郑氏胡说》,以培训我的口才,将我打造成教师以及将我的所有作品命名为《皮皮鲁总动员》后交给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和创办皮皮鲁讲堂。他18岁后做的以上这些事,除了在报社的三年外,都属于通过将我的资源扩大延伸体现他的价值。
前些天,郑亚旗给我打电话说他在北京建造了一座硕大的摄影棚,他问我愿不愿意去照几张相。近一两年我有时见到他背着各种照相机,我以为只是玩玩。最近看到他的博客以摄影为主要内容,我有点儿感到意外,得知他建造了摄影棚,我才知道他又另起炉灶了。
我去他的摄影棚看了,各种专业摄影设施一应俱全,摄影棚大到能开进去几辆汽车,还有小型电影院。到郑亚旗摄影棚照相的人络绎不绝,需要提前一个月预约。在他的摄影棚,郑亚旗给我照了几张相。置身于和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的另类“炉灶”中,我的感觉很是奇特。
我的父亲不是作家。我不是摄影师。为人父的榜样作用不是鼓励后代模仿和照搬,而是刺激后代在继承中变革。我不知道我的孙辈会从事什么职业,但我相信从小目睹父亲郑亚旗身教的他(她),会敬业和自食其力,因为我们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