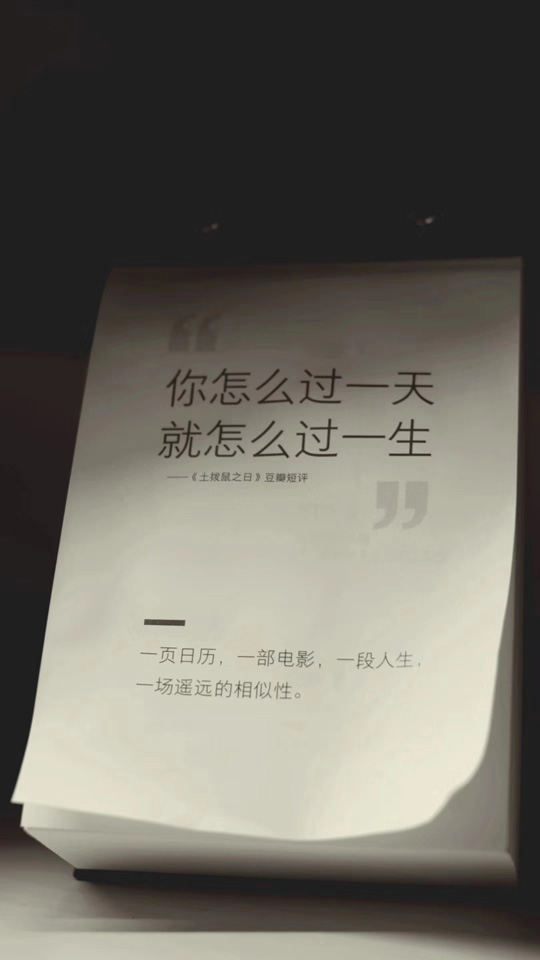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从镇上步行十几里山路去支农蹲点的山田村。走到半路时,我在一块干净的大石头上坐下来歇息,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却怎么也找不到打火机。
这时过来一位年近花甲、肩挑稻草的农民。我赶忙起来打招呼:“大叔,身上有火柴么?”
他看了我一眼说:“有,”把一盒火柴递给我,然后把担子转到另一个肩上,继续往前走。
我说:“大叔,坐下来歇会儿抽支烟吧。”
他说:“谢谢,我不吸烟。”
我点着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才想起火柴在自己手上。我追上去喊:“大叔,对不起,忘了把火柴还你啦!”
他说:“没关系,你拿着用吧!”并顺便问我:“大热天去哪儿?”
我说:“去山田村。”
他说:“还有好几里路呢,你还不得抽几支烟。”
我说:“没关系,到前面再买。”
他笑了笑说:“你是第一次来这地方吧,前面没人家,一时半会儿到哪儿买去,你就拿着用吧。”
我过意不去,于是就问:“大叔,请问你尊姓大名?”
他减慢速度,回过头来对我说:“庄户人家哪敢称什么尊姓大名,村里人都叫我‘追风汉’”。
半个月之后,阶段性工作结束,我从山田村赶回县城,途经杏田村,特意拐了进去,并带去一包火柴。
找到“追风大叔”,他正从菜园里出来,看到我,忙搬了椅子让我坐,我忙说:“大叔别客气,今天我有事,得赶回县城去”,说完,拿出那包火柴放在椅子上。
第二年春天,我又被调到春耕工作组,还是在那个偏僻的山田村。从县城走了三个小时,到了杏田村已经是下午四点多,可越急路越跟你过不去。开着开着,车子“扑通”一声滑到旁边的烂泥坑里去了。我们只好脱了鞋袜挽起裤腿下去推车,可无论怎么推,也无济于事,而且车子越陷越深。眼看着天色不早,我们商量着去前面的杏田村借几把锄头和铁锨来。
我走到村口的一户人家,见一个小伙子正在洗脚,便上前借锄头。那小伙子冷冷地瞧了我一眼说:“对不起,我们家的锄头全拿到铁匠店修去了。”我又走到一户人家,再次冲站在门口的一位中年妇女借锄头,那妇女瞪了我一眼说:“对不起,锄头让男人拿到地里干活去了。”
就这样一连走了几家都以种种理由被拒绝了。我只好去找“追风大叔”,大叔一家正准备吃饭,我一进门,他就认出来了。“这不是岩同志吗?来来来,一起吃饭。”
我忙说:“不,不,我们的吉普车陷在你们村边烂泥坑里了,想借几把铁锨和锄头把泥挖开,把车子推上来。”
追风大叔“啊”了一声说:“那好办。”接着命令几个孩子:“都帮岩同志推车去!”
我说:“大叔,不用了,你们吃饭吧,只请你们帮忙借几把铁锨和锄头就行,我们车上还有几个人呢!”
“追风大叔”不容分说地拉上我:“走!我多叫几个人一同去。”他走在前头,一会儿进这家喊几句:“永发侄在家吗?带上你们的锄头,帮岩同志推车去。”一会儿跑到那家叫一声:“茂生在家吗?拿着你们的铁锨,帮忙推车去。”
不一会儿,就来了七八个壮劳力。到了吉普车旁,开沟地开沟,挖泥地挖泥,四个轱辘全清理出来后,“追风大叔”在一旁指挥着:“左边站两个,右边站两个,其余都站在车子后面去,我喊一声‘推’,你们一起用力……”
车子很快被推上了路,这时我听到身后一位村民说:“这位可能就是‘追风大叔’经常提起的借一盒火柴还十盒的岩同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