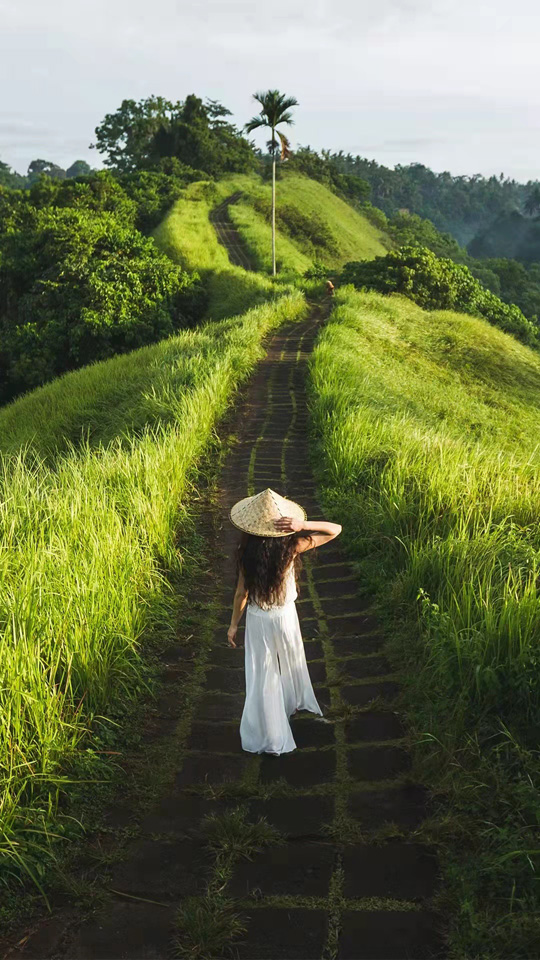这件事曾经残酷地摧毁了我
到目前为止,我的生命被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之前和20岁之后。
19岁那一年,我最好的朋友得了肝癌。那是我第一次如此真实地感受到死亡的存在。当时,她在荷兰留学。在荷兰,安乐死是一种合法的行为。因为已到肝癌晚期,病魔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她,疼得实在受不了,她甚至会咬自己的胳膊。所以,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求我为她签署安乐死同意书。
我那个时候太年轻,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承担得起对另外一个生命的责任。在万般无奈下,我狠心为她签署了一份安乐死同意书。
这个决定,由此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在她的追悼会上,当人们得知是我为她签署了安乐死同意书时,可怕的一幕出现了,我至今都无法忘怀。他们说,是我杀了她,他们说,我一定会得到报应。开始是一个人、两个人,到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我进行谴责。
在此之前,我每天都因为好友的去世而哭泣,用医生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人遇到这种事情时的正常反应;而自从追悼会后,我没有再对此说过一句话,我感觉自己已经无力面对这个世界。自我封闭,成了我保护自己的唯一方式。我每天都躲在屋子里,拉上窗帘,不和任何人打交道,也不和父母说话,只是每天坐在地上,问老天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那一年,我被确诊为“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是一种很严重的心理疾病。
经过一年半炼狱般的治疗,精神鉴定中心为我开具了一份已经康复的鉴定书,但实际上,我知道我并没有康复,因为我对死亡仍然有着非常深的恐惧。
死亡,它曾经这样无情而残酷地摧毁了我,我一定要认清楚它的真面目,我要看看它为什么会让我变成那个样子。所以,后来我做了一个决定,要去离死亡最近的地方——临终关怀医院,去了解死亡的真相。
因此,我在21岁的时候,成了一名临终关怀志愿者。要清醒地活在当下
至今,作为一名临终关怀志愿者,我已经送走了几十位临终者。
我曾经以为,我是去与死亡对抗的,但没想到,最后我和它握手言和。
在临终关怀医院里,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死亡。有的人很平静地面对死亡这件事,有的人很挣扎、很折腾,也有的人活得很精彩。他们都以自己不同的方式,走向死亡。
在我服务的对象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林的奶奶。她是一位很有智慧的老太太,她常常对我说:“生命自有它的定数,我们要承认,生命就到这里了,我们就允许它到这里。”有很多次,她在深夜拉着我的手说:“如果有一天,在我生命的最后阶段,我意识不清楚了,我煳涂了,千万千万不要给我治疗,我不想看着我的血一点点变成黑色,我想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我发现有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大多数子女在父母病危或临终时都不愿意放手。后来,林奶奶的癌细胞扩散了,她的女儿一定要让她去做化疗,林奶奶不愿意,就用自残来抵抗。最后,她女儿看她这么坚决,才含泪不再逼林奶奶去做化疗。
在临终关怀医院,我听到很多家属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我今天不给他治疗,我将来会后悔的。”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我们不能允许生命就这样轻易地终结,我们希望生命永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可是事实上,生命终将会终结,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渐渐明白,死亡有很多种维度,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是非黑即白的,一定是绝望的、悲伤的。
我常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你天天和一群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人生活在一起,你是如何调节自己的悲伤情绪的?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后来我就想:为什么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就一定要有悲伤的情绪呢?因为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死亡是一件绝望而悲伤的事情。但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死亡不再是让人恐惧的。
就像那位林奶奶,她之所以能够这样镇定而从容地面对死亡,是因为她已经深深领悟了生与死的意义。在临终关怀医院志愿服务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其实取决于他活着的时候。死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着。你可以好好地活,才能够好好地死,你只有清醒地活在当下,才能够勇敢地告别这个世界。
生命只有一次,但是我们曾经无数次地在影视作品中体验和直面死亡。对死亡的感知与体验,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活着。
我非常不赞成这个观点——好死不如赖活着。任何时候,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我都不会选择苟且地活着。
我认为我活着的意义就是:风风光光地来到这个世界,坦坦荡荡地活着;然后在我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可以有尊严地、安详地离开,不枉我曾经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