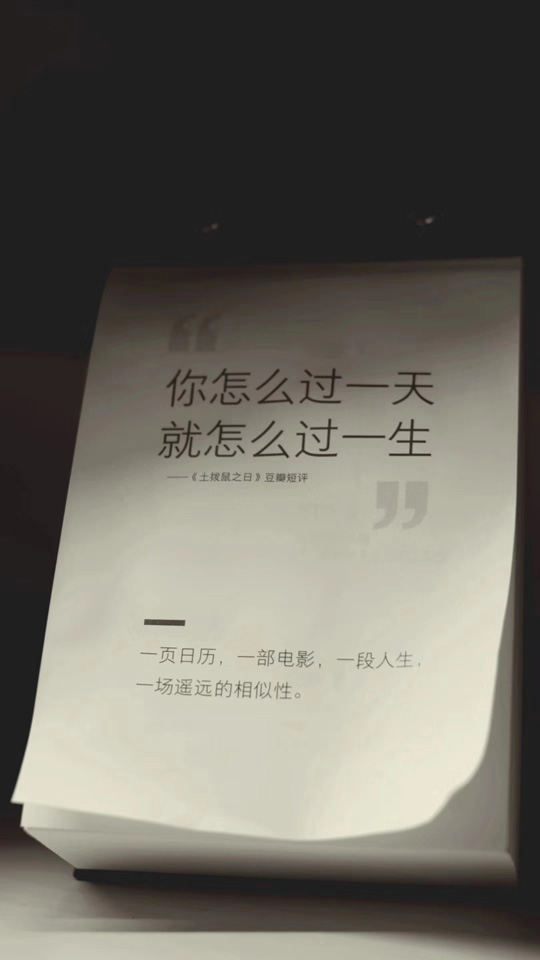天就要黑了,周遭暮色渐浓。落日也早被晚风带去远方,只将疲倦留给满城昏黄的灯火。
我从浮世退回陋室,抖落满身尘埃,锁紧斑驳的绿皮铁门,恐惧瞬间将我包围。整整十年时间,我都蜗居在仅有三十平方米的房间里,看书、写作、睡觉和冥想,忍受着人世的孤独。
我的亲人不在身边,他们全在县城生活,我们之间的联系,便是思念和记忆,以及对周末见面的期许。所幸家人都很宽容,都理解我,既无责备,也无埋怨——生存就是不断地相聚和别离。
像我这种从乡下闯入城市之人,没有丝毫优越感可言。我所获的尊严和安身立命之地,都是我长年累月在生活的炼狱里打拼得来的,绝非来自家族的馈赠。
我的存在即我的命运之门。
我知道,我的家人也会牵挂我。许多时候,奶奶会坐在老家的屋檐下,望着风中飘飞的落叶,或夜晚稀疏的星辰,暗自祈祷或垂泪;父亲会在夕阳的余光下,孤单地走在凄清的乡村公路上,目光深邃地朝我寄身的城市方向眺望;母亲则会在夜幕降临之后,坐在灯光下翻看那本珍藏了几十年的老相册,用粗糙的手在我幼时的照片上摩挲;妻子不管时间多晚,都要在入睡前跟我通个电话——我们在电话里或许什么事都没说,但通完电话心就安宁了,就不会再躲进被窝哭泣;至于我的两个儿子,也跟他们的母亲一样,每晚都要跟我在电话里说上几句才能入眠,不然,他们就会在梦中喊爸爸——那稚嫩的声音,可以将黑夜撕成一床破棉絮。
人到中年,我才真正认识到活着的困境。
我不只属于自己,也属于家人。我被他们分成好几份,每一份对他们来说都至关重要。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我,地球依然会转动;但如果家人没有我,他们一定会重返生存的荒原,会顿觉失去了活着的意义。反过来说,假使没有他们,我活着,同样会是一片空白和虚无,犹如掉进时间的黑洞。
因之,我活着就不单单是我活着,我还在为我爱和爱我的人而活。
活着是有限的存在,唯有爱是无限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