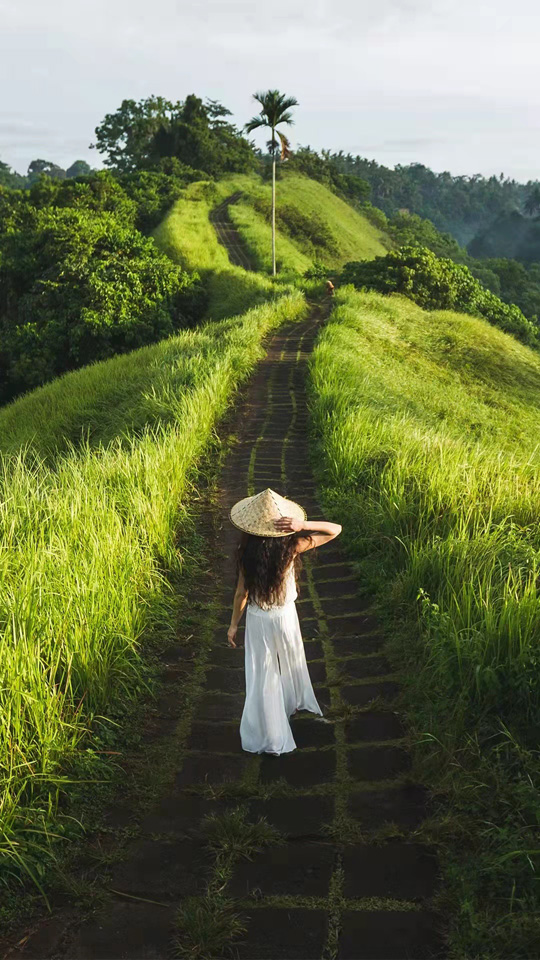可能是年龄大了的原因,明白了人的生命的长短,也爱回忆起往事来,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不,又想起了我的奶奶来。
我自打出生到懂事起,就没有见过爷爷,因为爷爷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因病离世了,但奶奶还在世。在我童年的印象中,家里的老人也就奶奶一人,奶奶名字叫王凤英,在“家谱”里头只有“王氏”两字。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奶奶没有和我们同住一屋,而是独自一人住在我们家老西屋右侧的一间草房里。草房共有两间,一间是我们家的厨房,我们都叫它“小厨屋”,一间是奶奶住的。这两间草房之所以叫草房,就是因为房顶全都是用麦秸、泥巴和在一起铺盖而成的。墙壁全部用泥巴垛成,虽说是泥巴垛成,但墙体却很厚,屋内冬暖夏凉。奇怪的是,两间面南背北的草房却没有留一个窗户。当然,也有可能是还是为了安全所致,也有可能是为了节约材料。
我们家一家七口人,父母、姐姐、大哥、二哥、弟弟和我,住在三间西屋混砖结构的房子里。说是混砖结构,就是砖少,泥垛多,唯有墙根及房屋的四角是砖砌成的,其它全部是黄土和成的泥巴剁成的,墙体虽然比较厚,但屋内空间却很狭窄,并不宽敞,这也可能是奶奶不方便和我们居住在一起的原因。她住的那间草房子虽小,但算是有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和住处,生活起居很是自由方便。
在我的记忆里,奶奶那时已经进入老年,六十岁出头,个子不是太高,大概有一米五左右,用布裹脚,是传统的小脚女人,走起路来不是太快,但也不是太慢。
在她有生的时间里,我从未见过他穿过花衣服,也就是五颜六色的衣服。无论是哪个季节,她所穿的衣服总是黑色或白色,黑色的居多,白色的少。冬天或是秋天,她头顶上总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帽前还有个铜钱般大小的白色标志。
让我感觉奇怪的是,奶奶说话的口音和我们略有不同,后来我才知道,奶奶并非我们本地人,那时父亲的常说的一个地名,就是东南滩,奶奶是东南滩人,也就是现在的原阳县蒋庄公社杨厂村人。
为何叫东南滩?可能是它地处我们家乡的东南部,在黄河的边上,杨厂村地处黄河的北岸,土地多为河滩,距离黄河很近,因此父亲常称它为东南滩。
东南滩距离我们家乡千村大概有30公里左右,如果放在现在,有很多交通工具,走个亲戚应该不算太难,但那时没有交通工具,走路全靠两条腿,所以,奶奶的娘家在我们家人看来应该是最远的亲戚了。因此,每年除了过年或麦罢(也就是麦收时),平时很少相互走动,因为的确是感觉太远了。早上天不亮开始走,走完亲戚往回赶,即使走的速度快,回到家也到天黑了。
据母亲说,奶奶有次一人去娘家,早上天蒙蒙亮就走,风尘仆仆,走到了杨厂村,连头上的簪子丢了都不知道,满头发都是露水。因为路太远,走路太累,父亲一年的时间,和奶奶一起最多去两次。
那时父亲的两个舅舅还都在世,家人也不少。另外,父亲还有个姨妈,住在黄河大堤堤南何营公社,一个叫郭庵的村子里,位于原阳县蒋庄公社杨厂村的西部,距离我们家乡武陟县乔庙公社千村稍微近一点。
奶奶当时的牙齿近乎掉光,残缺不齐的仅有几颗,说话始终带着原阳口音,虽然和我们说话有所不同,但她说话的意思我基本上都能够听得懂,她很少说我们家乡的一些土话,多半是原阳方言。
奶奶毕竟和我们家七口人不是同住在一个屋子里,虽说是同一院子,她却很少主动到我们所居住的三间西屋里来,也很少同我们说话,即便是在院子里见到了,说话也不多,但我却动不动爱往奶奶居住的那间草房子里跑,奶奶见了我话也不多,顶多也就是吃饭了没有?不要乱动屋里的东西!没有疼爱我这个孙子的任何举动。在这一点,我总觉得她和邻居家的奶奶就有所不同,邻居家的奶奶会通过各种言语或举动,体现出对孙辈们的疼爱有加。
我想也可能那时我们家生活太贫穷,奶奶生活的不是太如意,心情也没有那么好,这是主要原因。
贫穷的农民家庭,多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表面上或是忧伤,或是凄苦,不如意的有八九。
在我的印象里,奶奶当时头发大都花白,皮肤黝黑,身材佝偻。她虽然是缠足小脚,却经常爱到地里去,去干啥了也不知道。每当她从地里回来时,总能看到她手上少不了要拾把柴禾,是用来家里烧火做饭用的,因为在她住的一间草屋里,我看到有一个小锅台,还有锅碗瓢勺筷子。
有一天,我在离家不远的邻居家的房后,看到一只小死狗,就从家里拿来一把把子不长的圆头铁钎,准备在那房后的空地上挖个坑,将小死狗埋起来。正在挖坑时,被从旁边的路上,刚地里回来的奶奶在看到了,他手里仍然是拿着把式的柴火棒,朝着我和小伙伴直喊:“可不敢埋,不敢埋,买了它会成狗精,成狗精了会咬人!”
我吓的赶紧停了手,没有再埋小死狗。我也不知道奶奶说的成狗精会成什么样的狗精,但是感觉到那狗精会很厉害,对奶奶的话我是十分相信的,心里暗自庆幸还没有将小死狗埋掉,否则小死狗成精了,可能会真的找我“算账”。
再后来,我就发现奶奶可能是患重病了,经常躺在那间小草屋的床上,很少出门了。那天,我跑到奶奶的小草屋里,走奶奶的床前。奶奶睁开闭着的双眼,看着我,把手从被窝里缓慢地抽出来,用手指着床头边上小木板的一半苹果,用很微弱的声音对我说:“你吃吧!”
在朦朦胧胧中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家里来了很多人,都是些本家的乡邻们,奶奶也破天荒地躺在了我们家那三间西屋的正当屋中央的小床上,头朝外,脚朝里,床头的小桌子上,放着几碗供品。
奶奶穿着一套黑衣服,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她躺在那里,很是安详,像是睡着了似的。母亲在奶奶身边小声喊着说:“妈!把你哩手松开,把你哩手巾拿住!”原来是母亲要把奶奶握着的手掰开,让她手里拿着自己的手绢儿。
我这才意识到,奶奶已经是去世了,但从母亲的话语中感觉奶奶还跟活着一样。
我们全家人,还有一些本家自己,还有亲戚,在西屋里为奶奶守灵。西屋的地上铺满了稻草,我们全家人,还有本家自己,亲戚,都是些亲近的人,在稻草上,或躺或坐了两晚上,为奶奶守了两天的灵。
第三天的早上,我跑到我们家两间草屋后面叔叔家的院子,发现有一口新做好的白木新棺材,那盖子在棺材之上,是错开放着的。
在一棵榆树上,拴着一头毛驴,堂哥海军说是老舅来了,老舅也就是奶奶的亲弟弟,从东南滩过来了,因为路途太远,老舅和家人,是用小毛驴套着一辆小木板车过来的。
我看到那棵榆树上拴着的小毛驴儿正在吃草。究竟是大老舅,还是二老舅来了,我不太清楚,总之是奶奶的娘家人来了,我不知道本家人是谁去给奶奶娘家报的丧?
到了上午,奶奶要起灵下葬了。
在亲人们的哭喊声中,奶奶的棺材被“咚、咚”的大铁锤钉上了盖子。棺材的上面蒙了一层鲜红的红布,被乡亲从西屋抬到了院子,又被从院子抬到了院外门口的路上。此刻,母亲“哐当”将垴盆摔在地上砸了个碎,棺材被乡亲们簇拥着抬起,父亲抬棺材大头,本家一群亲人哭天喊地,跟在前面乡亲们抬着的奶奶的棺材后面。我也傻乎乎地跟在后面跑,但心里也同样充满了悲伤,想着奶奶今生今世可能再也看不到了,两眼噙满了泪水。
乡亲们抬着奶奶的棺材,来到了村东北的我们千家的老坟地,奶奶的墓穴早已被挖好,那挖出来的黄土,还显露着湿漉漉的颜色。
我亲眼看着,奶奶的棺材被乡亲们用绳子拉着,很慢、很慢地放到墓穴中。刚开始,家人和亲人们是用手一把土一把土地往墓坑里撒,接着是请来帮忙的乡亲们用铁锨往棺材上填土,且填土的速度很快。不一会儿,奶奶的棺材,就被埋在了土里看不见了,外面只留下了一个大坟堆。
奶奶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也就从那时,我才知道人还会有死的概念,任何人都不会长生不老。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奶奶,我童年时距离我最近的挚爱老人,也是让我感到最为痛心的老人。
因为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全家人生活条件都很差,奶奶没有条件享上清福,正是因为贫穷,她才过早的因病去世,因为她六十多岁的年纪,无论是在那时,还是在现在,都不算是高寿,如果生活条件好一点,奶奶,还有我那从未见过的爷爷,也就不会因患病而过早地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