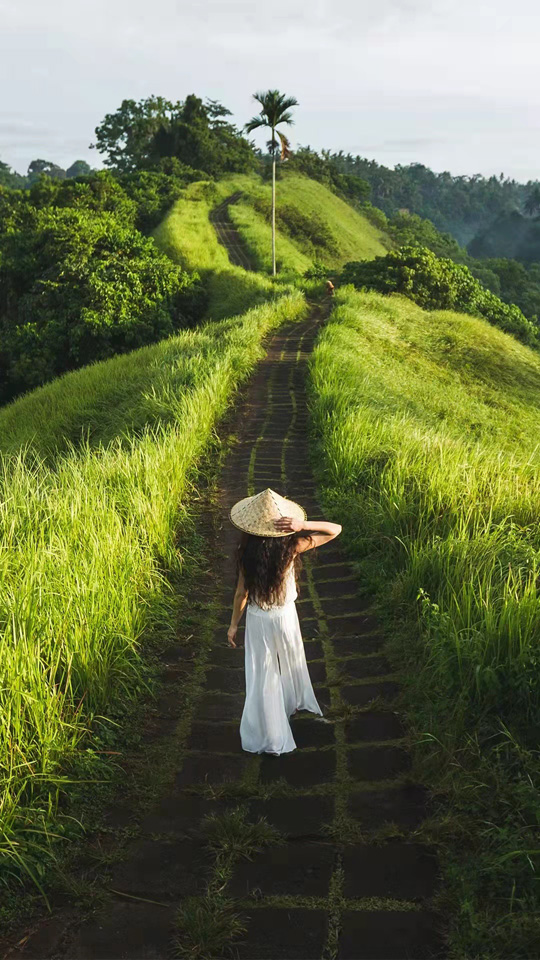高三那年,和父亲再次聊起未来。他希望我学医学、法律或者理工科,这些东西经世致用,也意味着好工作。至于我一直喜欢的文学,他不以为然:搞文学的最后都饿死了。
他的语气从来都是不容置疑的,我也从未吐露过不满。那一次,或许是学习压力太大,我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呛了他。军人出身的父亲在震惊之余,掀翻了桌子。
我放下碗筷就往门外走,身后传来父亲的咆哮。沿着京九铁路线,我一直往南走,试图扒上一列火车,但它们都呼啸而过。天已经黑了,我愈发泄气,只好掉头往家走。到家已是后半夜,父母屋里的灯还亮着。母亲走出来,手指戳我的额头:“你们爷俩简直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那是1996年,在山东老家,同辈的孩子们没有人敢直接反驳父辈,最“忤逆”的方式是私自行事。填写高考志愿时,我偷偷写上了“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到来,是家里气氛最阴沉的一天。他站在院子里铁青着脸,没有拿鞭子抽我,但半个月没跟我说话。后来每次见面,他话里话外都带着讥讽,尤其见我背了一整套文学名着回家,他会愠怒。在饭桌上,他不断提起自己当年在部队里的威风场面——曾有上万人听他一个人讲话。
我沉浸在被父亲打压的不忿里,从未注意过,其实他和这个家庭都在走下坡路。他所在的国营饲料厂效益大减,甚至无法一次性拿出我和哥哥一整年的学费和生活费。母亲念叨过,我的学费是父亲向厂里预支工资才拿到的,我以为她在开玩笑。
直到大四那年开学,父亲执意送我。坐上汽车的一刹那,我无意中回过头来,看到父亲穿着我军训时的绿军鞋,一根脚趾露在外面。而我记得军训过后,就把它丢到垃圾桶里了。那一刻我才明白,这个男人在背负着什么。
十一国庆大阅兵时,他打开一瓶酒,顺手给我倒了一杯。这是他第一次给我倒酒。我推托道:“我不喝酒的。”父亲的神情突然有些落寞,但还是说起当兵往事。只不过这一次,他讲的是那些糗事。我听了和母亲一起笑,家中氛围首次轻快起来。
过了几个月,我开始和父亲小酌。他再也没有讽刺过我的文学梦,反而告诉我,这条路不好走,要多多努力。我听街坊说,父亲经常在外炫耀我这个儿子,又写了多少文章,彷佛自己的脸上贴了金。但当着我的面,他从来不提我写了什么。其实我知道,我写的东西他都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