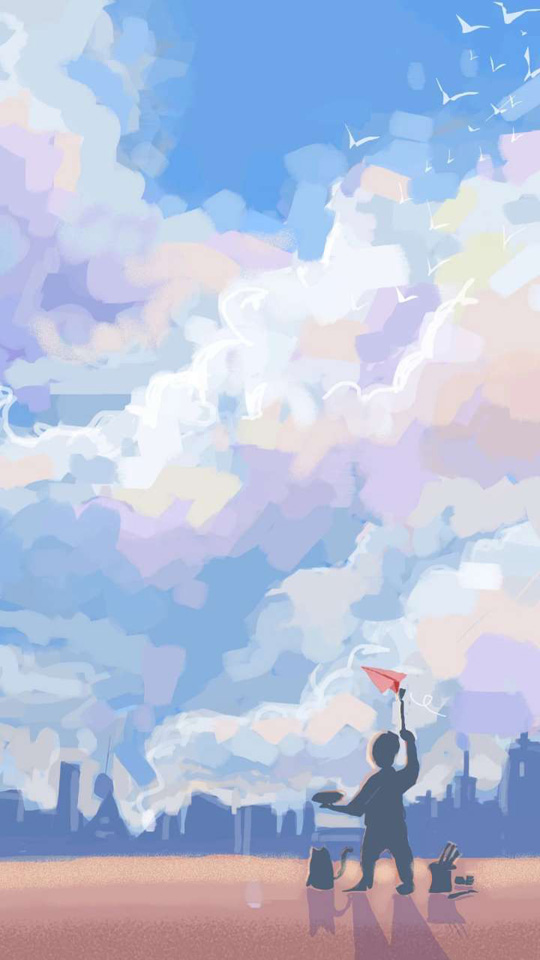在我9岁以前,外婆家还是外婆家。9岁以后,外婆家变成了外公家。原因很简单,外婆走了。每一个人都努力地在口头禅中抹去“去外婆家”的痕迹,于是变成了“去外公家吃西瓜吧”“今晚到外公家聚聚啊”。外婆刚走那两年,大家时不时还会顺嘴说错,就像每次跨年后在日记本上打开新的一页时,我总是习惯性地写成上一年的日期,又马上反应过来划掉。
“外婆”成了生活里的过去式,也被划掉了。
我不敢提起外婆,怕妈妈伤心;妈妈不敢提起外婆,怕外公和姨妈们伤心。每一年我们都需要辞旧迎新,但总有一些“旧”,我希望它一直在那儿。
有一段时间我总在想,对大多数人而言,当外公和外婆都健在时,为什么我们还是更喜欢用“外婆家”来指代?叶佳修写的是《外婆的澎湖湾》,周杰伦的《简单爱》里唱的词是“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看看”,大学时我很爱吃的那家连锁杭帮菜,也叫“外婆家”。
后来我明白了,“外婆家”和“外公家”是不一样的。虽然在物理空间上,两者指向同一处地域、同一栋老宅,但是“外婆家”就是不一样。
外婆家到了饭点,总有人喊我们:“小猴子们快下楼来吃饭啦!”外公家到了饭点,舅妈喊我们:“快去辉叔家把你们外公喊回来,他打牌打得又忘记吃饭了。”
外婆家的客厅永远有充足的花生、瓜子和新鲜的小柑橘,我爱吃的山楂片和凤梨酥;外公家的茶几上有抽不完的水烟烟草,泡不完的铁观音茶叶。
外婆家的柴房顶上总有白猫跳过,柴门后放着外婆留给它和小猫们的晚餐;外公家不再有大猫或小猫光顾,外公举着大扫帚喊:“昨晚我在杂物房里看见好肥一只大老鼠!”
外婆家的出行工具是三轮车,外婆蹬着它,带我和小板凳一起去市场,又载着我、小板凳和买的菜一起回家,一边蹬车一边说:“今晚吃溪妹妹最爱的鱼丸。”外公家的出行工具是“哼哧哼哧”的老式摩托车,前面装着大大的油瓶,刚好还能放下外公的脚,后面的座位大概只有一块砖头那么大,还是硬硬的金属板。我们嫌它太硌屁股,外公不好意思地,露出缺了一颗牙的笑容。
外婆家的枕头有香香的阳光味,蓝色碎花枕套里装着每年新鲜采下的“阳光叶”。细细长长的树叶子,被晒得松脆又清香。夜里睡得闷热时翻个身,耳畔便响起风摇动树叶般的声音,沙沙沙沙,叶子们唱起晒太阳时的歌。
外公家的枕头是硬邦邦的竹枕,蜂蜜色的小方块棋盘般排列好,像整齐的牙齿。等你睡着时,它便悄悄张开嘴咬牙切齿,一口夹住你的头发丝,所以每次起床时都必须向它上缴几根头发。
外婆的照片,被高高地摆放在大门正对着的八仙桌上方,和挂钟一样高。
外公从来没说过想念外婆。但他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搬来木梯,爬上去,在神龛里点上三炷香,稳稳地插在照片前,再轻轻擦去镜框上的灰尘。
那时候的我觉得外公就像动画片里的机械表。一到早上起床的时候,他就像那只一到整点便从挂钟里准时弹出的小鸟一样,敬业而忠诚地搬来木梯,完成他一天的仪式。只是,外公和久未保养的机械表一样,渐渐变慢。外公的腰越来越弯,爬上去再爬下来所用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后来,大家不让外公上去了。听完女儿们的决定,外公站在一旁沉着脸,不说话。满满弟弟突然说:“以后我上去吧。”外公的眼睛亮了起来,满满弟弟就这么接替了外公的“职位”。外婆走的那年,满满弟弟才6岁。今年他18岁了,长得比外公、比舅舅都高。
老宅也迎来了新的脚步声、哭声和笑声。外婆走后的第6年,小姨又怀孕了,在我中考完的那个暑假,诞下了一位哭声响亮、眼睛大大的糖妹妹。老宅的客厅里不再只有抗日剧的寂寞声音,糖妹妹在沙发上爬着,在茶几前跳舞,挥摆着肉肉的小手。她坐在外公腿上摸他硬硬的灰色胡子,把外公逗得哈哈大笑。
我们都舍不得把目光从糖妹妹身上移走。她走到哪里,我们一大群人就像跟屁虫一样跟到哪里。外公把他那辆已经老得喘不上气的“硌屁股”摩托车,换成了平稳舒服的小电驴,每天去幼儿园接糖妹妹放学。
糖妹妹没有见过外婆,但她一定知道外婆很爱她。因为她最爱来外公家;因为外公家的每一个人,都很爱她;因为在很久以前,外公家也是我们最爱的外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