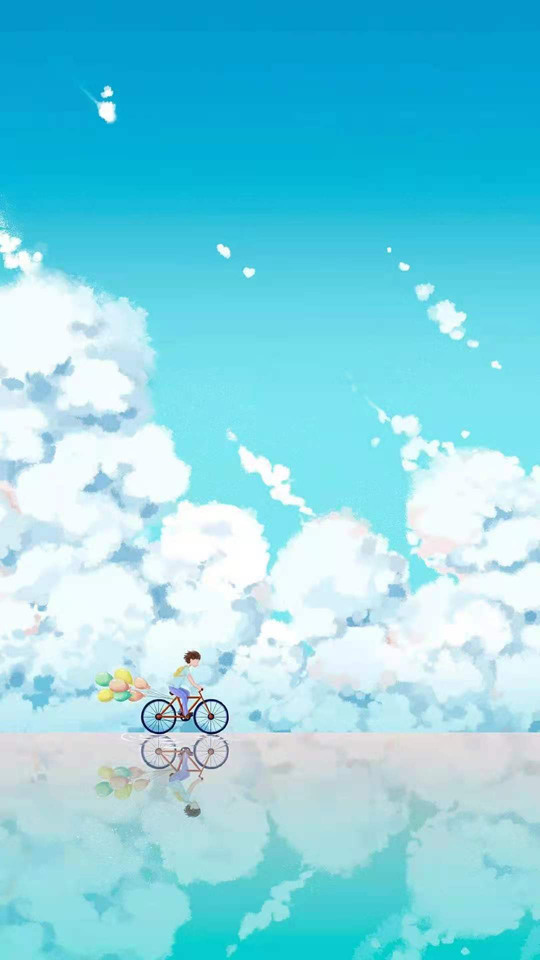母亲怎么也没有想到,十九岁的我,要离开家乡到北京读书。她事先完全没有准备,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不但在她的想象中,而且在我的想象中,北京简直就像天边一样遥远。
1955年,福建还不通火车。从我家乡连城县出发,要坐五天的长途汽车,才能到达有火车的江西鹰潭。山高路险,行程艰难。“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毛泽东的词句所描写的路,正是我去北京的必经之途。那时候,我们那里的人去一趟北京,感觉上比我们现在去一趟西欧、北美还要遥远得多。记得我在龙岩读中等师范学校时,有一位老师长途跋涉去北京开了一次会,就像出了一次国似的,回来后在全校做了一个报告,专门讲在北京的见闻。至今我还记得,他津津有味地讲北京冬天街道两旁的树干,都涂了像人一样高的白灰,远远望去,像一排排穿着白衣的护士整齐地站着。
我去北京读书的消息,经乡亲们渲染,变得“十分重大”。祖母和母亲手足无措,心绪不宁,不知该为我准备什么好,更有一种生离死别之感盘桓在她们心间,折磨她们。可理智上她们又觉得儿孙“进京”读书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是不能轻易哭的,离别的痛苦只能忍着。所以我离开家时,祖母始终是平静的,起码表面上如此。
我出发那天,母亲要送我到离我们村子十五里的朋口镇去搭汽车。她着意打扮了一番,穿一身新的士林蓝布衫,脸上搽了白粉,嘴唇也好像用红纸染过,脑后圆圆的发髻上还一左一右插了两朵鲜红的花,让人觉得喜气洋洋。那十五里路我们是如何走过来的,在我的记忆中已很模糊了。唯有在汽车开动前,母亲“空前绝后”的哭和止不住的眼泪,至今仍历历在目。她拉住我的手,语无伦次地说:“北京‘寒人’(冷),要多着衫。实在有困难要写信给家里讲,我会给你寄布鞋。我知道你惦记祖母,不要惦记,有我呢。也不要惦记弟弟妹妹,有我呢。读书是好事,要发奋,光宗耀祖。毕业时写信来,让你爸写‘捷报’,在祖宗祠堂贴红榜,大学毕业就是‘进士’,就是‘状元’‘榜眼’‘探花’……”说着说着,她突然流下了泪,而且那泪像家门口的小溪那样滔滔汩汩,堵不住,擦不完,完全失控,后来母亲竟失声痛哭。她的哭就如同蓄积已久的感情的闸门被开启,非一泻到底不可了……后来她不再擦她的眼泪,任其在脸上自然流淌。她哭着,嘴里还说着什么,但我已经听不清楚了。我只觉得自己无能,在这个时候竟说不出一句恰当而有力量的话来劝慰母亲,只是傻傻地待着,还轻声说:“妈,你别哭了!人家看咱们呢!”谢天谢地,汽车终于开动了,她似乎意识到离别终成事实,便举起了手。我从车窗探出头,看见她泪流满面,这时我发现自己的眼睛也湿润了。她不由自主地向前跑了几步,但汽车加速了,她向后退去。在第一个拐弯处,她的脸在我的视线中变得模糊了,但我仍清楚地看见,她头上的那两朵红花在晨风中轻轻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