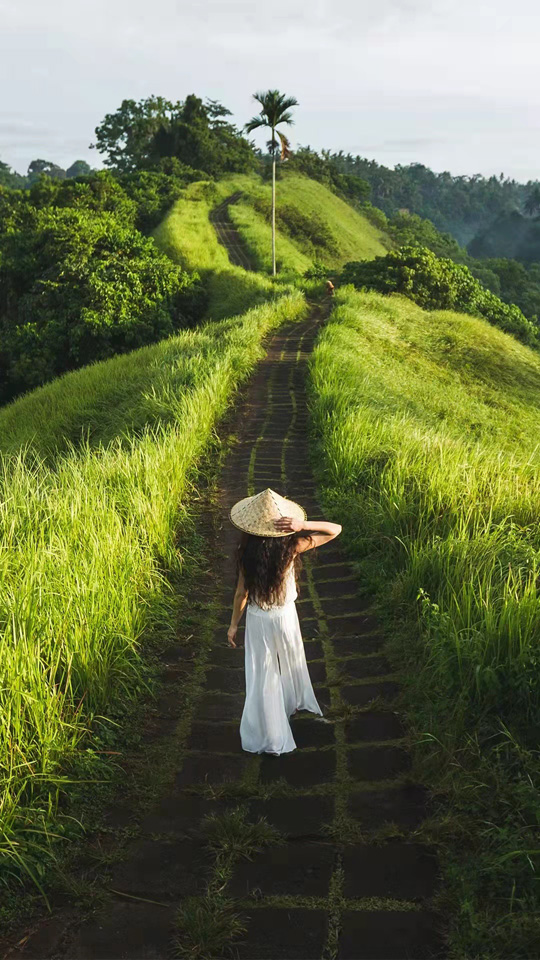最后,日子还是得一日三餐地过下去,便只好走进母亲的厨房,虽然母亲1987年就从厨房退役,但她在世和刚刚走开的日子里,我总觉得厨房还是母亲的。每一家的厨房,只要有母亲还在,就一定是母亲的。
我站在厨房里,为从老厨房带过来的一刀、一铲、一瓢、一碗,一筷、一勺伤情。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不是母亲用过的。
也为母亲没能见到这新厨房和新厨房里的每一样新东西而嘴里发苦,心里发灰。
为新厨房置办这四个火眼带烤箱炉子的时候,母亲还健在,我曾夸下海口:“妈,等咱们搬进新家,我给您烤蛋糕,烤鸡吃。”
看看厨房的地面,也是怕母亲上了年纪腿脚不便,铺了防滑的釉砖。可是,母亲根本就没能走进这个新家。
分到这套房子以后,我没带母亲来看过。总想装修好了,搬完家,布置好了再让她进来,给她一个惊喜。后来她住进了医院,又想她出院的时候,把她从医院直接接到新家。
可是我让那家装修公司给坑了。
谁让我老是相信装修公司的鬼话,以为不久就能搬进新家,手上只留了几件日常换洗的衣服,谁又料到手术非常成功的母亲会突然去世,以至她上路的时候,连一套像样的衣服也没能穿上,更不要说是她最喜欢的那套。
厨房里的每一件家什都毫不留情地对我说:现在,终于到了你单独来对付日子的时候了。
我觉得无从下手。
翻出母亲的菜谱,每一页都像被油炝过的葱花,四边焦黄,我从那上面,仍然能嗅到母亲调出的油、盐、酱、醋,人生百味。
也想起母亲穿着用我那件劳动布旧大衣改制的又长又大,取其坚牢久远的围裙,戴着老花镜,伏身在厨房的碗柜上看菜谱的情景。
这副花镜,真还有一段故事。
那次,母亲到新街口邮局去,回家以后,她发现花镜丢了!
用母亲的话说,我们那时可谓穷得叮当乱响,更何况配眼镜时,我坚持要最好的镜片。别的我不懂,我只知道,眼睛对人是非常重要的器官。1966年那个时候,那副13块多钱的镜片,可以说是花镜片里最好的片子了。回家以后,她失魂落魄地对我说到丢了眼镜的事,丢了这样贵的眼镜,母亲可不觉得就像犯了万死大罪。
花镜不像近视镜,特别是母亲的花镜,那时的度数还不很深,又仅仅是花而已,大多数老人都可通用。尽管那时已经大力开展了学雷锋的运动,只怪母亲的运气不佳,始终没有碰上一个活雷锋。
每每想起生活给母亲的这些折磨,我就仇恨这个生活。
后配的这副眼镜,一直用到她的眼睛用什么眼镜都不行了的时候,再到眼镜店去配眼镜,根本就测不出度数了。我央求验光的人,好歹给算个度数。勉强配了一副,是纯粹的摆设了。
这个摆设,已经带给她最爱的人,作为最后的纪念了,而她前前后后,为之苦恼了许久的这副后配的眼镜,连同它破败的盒子,我将保存到我也不在了的时候。那不但是母亲的念物,也是我们那个时期的生活的念物。
母亲的菜谱上,有些菜目用铅笔或钢笔画了勾,就像给学生判作业打的对勾。
那些铅笔画的勾子,下笔处滑出一个起伏,又潇洒地扬起它们的长尾,直挥东北,带着当了一辈子教员的母亲的自如。
那些钢笔画的勾子,像是吓得不轻,哆哆嗦嗦地走出把握不稳的笔尖,小心地、拘谨地、生怕打搅了谁似地缩在菜目的后面而不是前面,个个都是母亲这一辈子的注脚,就是用水刷、用火燎、用刀刮也抹灭不了了。
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用铅笔画的勾子和用钢笔画的勾子会有这样的不同。
那些画着勾子的菜目,都是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菜,如糖醋肉片、软溜肉片、粉皮凉拌白肉、炒猪肝、西红柿黄焖牛肉。鱼虾类的菜谱里,档次最高的也不过是豆瓣鲜鱼,剩下的不是煎蒸带鱼,就是香肥带鱼。至于虾、蟹、鳖等等是想都不想的。不是不敢想,而是我们早就坚决、果断地切断了脑子里的这部分线路。
不过我们家从切几片白菜帮子用盐腌腌就是一道菜,到照着菜谱做菜,已经是鸟枪换炮了。
其实,像西红柿黄焖牛肉、葱花饼、家常饼、炒饼、花卷、绿豆米粥、炸荷豆蛋,母亲早已炉火纯青,其他各项,没有一样付诸实践。
我一次次、一页页地翻看着母亲的菜谱,看着那些画着勾,本打算给我们做,而又不知道为什么终于没有做过的菜目,这样想过来,那样想过去,恐怕还会不停地想下去。
我终究没能照着母亲的菜谱做出一份菜来。
一般是对付着过日子,面包、方便面、速冻饺子、馄饨之类的半成品也很方便,再就是期待着到什么地方蹭一顿,换换口味,吃回来又可以对付几天。
有时也到菜市场上去,东看看、西瞅瞅地无从下手,便提溜着一点什么意思也没有的东西回家了。回到家来,面对着那点什么意思也没有的东西,只好天天青菜、豆腐、黄瓜地“老三篇”。
做米饭是照着母亲的办法,手平铺在米上,水要漫过手面,或指尖触着米,水深至第一个指节,水量就算合适,但是好米和机米又有所不同,机米吃水更多。
我敢说,母亲的烙饼,饭馆都赶不上。她在世的时候我们老说,应该开一家“张老太太饼店”,以发扬光大母亲的技艺。每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是好事临门也还是愁眉苦脸的母亲,脸上便难得地放了光,就连她脸上的褶子,似乎也放平了许多。对她来说,任何好事如果不是和我们的快乐,乃至一时的高兴联系在一起的话,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还有母亲做的炸酱面。倒不因为那是自己母亲的手艺,不知母亲用的什么决窍,她烙的饼、炸的酱就是别具一格。也不是没有吃过烹调高手的烙饼和炸酱面,可就是做不出母亲的那个味儿。
心里明知,往日吃母亲的烙饼、炸酱面的欢乐,是跟着母亲永远地去了,可是每每吃到烙饼和炸酱面,就忍不住地想起母亲和母亲的烙饼、炸酱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