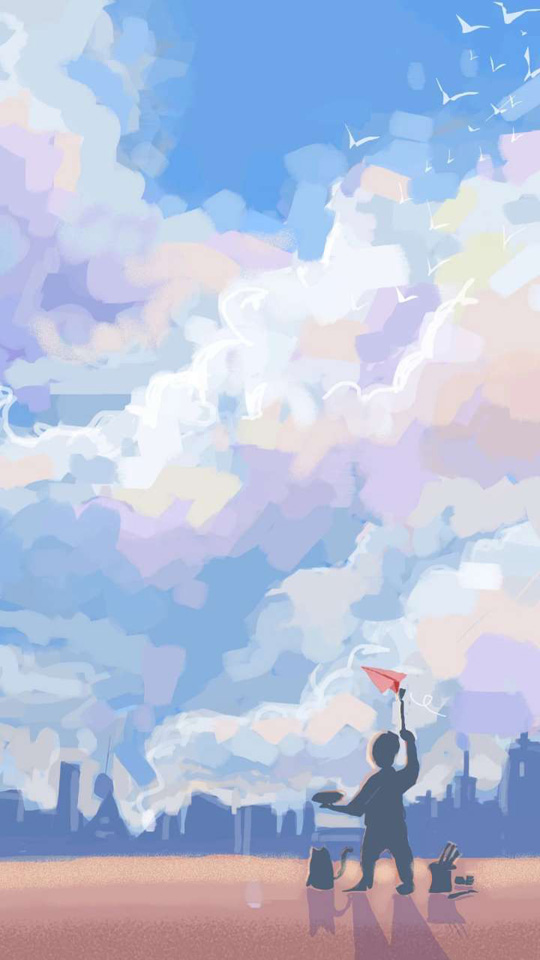外面是初冬的阴雨雪天气,据说今天大幅降温到零度。我和母亲都得了感冒,父亲在厨房静悄悄地做晚饭。
氤氲的热气在父亲银白色的头发上,他拿着筷子在挑动面条,很专注。我站在门边,满足地看着父亲,竟是看不够。先前父亲心脏发病住进了医院,想起已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当时母亲还在哈尔滨,赶不回来。我一个人在病房连待了三个晚上。父亲刚入院的三天,要连续打点滴,不能离人。前两天点滴里加了利尿剂,父亲常常二十来分钟就要从床上站起来尿一次,慢一点还要尿裤子,我只好用小便器给他接尿。第一次还不好意思,后来就习惯了,麻利得要命。一天到底多少次,我都记糊涂了。只是不停地接,不停地出去倒。晚上也几乎没合眼。
大夫查病源一直只在父亲二十年的糖尿病和高血压上打转,拼命用药,心跳却还是过快。一星期后,才查出父亲的甲亢复发也是心脏发病的一个重要诱因。医院用的虎狼药,把父亲吃什么都香的胃弄坏了。父亲天天吐,饭前吐一次,饭后吐一次,一天要吐七八次。我还是接了又倒,很麻利。
父亲在心脏病房天天打治胃的点滴,每天都要瘦一公斤。八天已经瘦了十公斤了。用父亲的话说,瘦得可怕。
好在病房还有两个可爱的将近七十岁的北京老人。两个老北京愿意带着父亲玩。我晚上快九点的时候不忍心把父亲一个人留在病房,穿上旅游鞋,跑到了医院。就看见病房里关着灯,父亲和左边的张老先生面对面趴在枕头上,在咕唧咕唧地说话。右边的最爱说话的刘老先生端坐着一脸严肃地举着不能外放的半导体收音机,带着耳机,在听世界杯的巴西对美国的半决赛。见我去了,他摘下耳机,对我说:“二比零了,美国队还罚下一个。现在中场休息。”
父亲住院,就像住进了一个幼儿园。不过,这个幼儿园的儿童每天要瘦一公斤还多,真是世界上最让人疼的孩子。
出院后的父亲,在大自然的风和阳光中徜徉了若干日。但是天渐渐变冷了,没有暖气,父亲又感到心脏不舒服,连续两晚不能入睡。那晚,父亲吃完药,睡了。我把朋友送的电暖器放在父亲的脚边,屋里从阴冷变得暖融融的了。我要一直等到凌晨三点。因为父亲通常心脏发病是从晚上十一点开始的。一到十一点,他就醒来不能入睡了,甚至不能平躺。时不时地,我悄悄走到父母的房门口,把耳朵贴在门上,听父亲的呼吸。母亲高一声,父亲低一声。母亲出声的时候,父亲不出声。母亲不出声了,父亲才出声。十一点、十二点、凌晨一点、凌晨二点、凌晨三点。父亲睡得很平稳,均匀地呼吸着,和母亲呼应着。
父亲的身体开始在好起来,似乎是一种意志使他在好起来。但不久,还是出了岔子。
前两天,我半夜十一点炖了一锅排骨。次日上午给父亲吃排骨,吃多了,父亲的脑子又糊涂了。只会说湖南家乡话,一串一串的。我和母亲一句都听不懂。父亲发现他说的话我们听不懂了,就更急,再说,我们还是不懂。作为一名制造飞机的工程师,父亲半个世纪前离开家乡到北方,已经不会说湖南话了,但在脑子出现障碍的时候,却只会说湖南话,而且是那么浓重的滚滚的乡音。
我和母亲从来没听父亲说过地道的湖南家乡话,真是惊心。但是我们都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不想再刺激他。母亲继续出门买馒头,准备午饭。父亲用湖南话说:“馒头。”,我就大声地坚决地用普通话说:“馒头。”父亲继续用湖南话说:“馒头。”我继续用普通话说:“馒头。”我打开电视,让父亲看他最爱看的中央四台的新闻节目。父亲用手示意,让我回自己的房间弄论文,断断续续地说:“走,……走。”
我隔一小会儿就去扒着门缝儿看,父亲在看电视,父亲坐在桌前吃柚子,父亲用手拂拭他弄乱的床单。我慢慢地推开门,父亲抬起头,明白地说:“我好了。”父亲又不会说湖南话了,只会说普通话,而且口齿比以前还利落。
父亲的生病终于告一段落了。只是脚和腿还有点肿,还不能出门。同时,我也得了经验,更多地知道了一点怎样照顾他了。我在路上看到老人,都非常亲。每个老人,就像一个篮子,那里面是多么沉重的一生的爱和付出啊。要多疼疼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