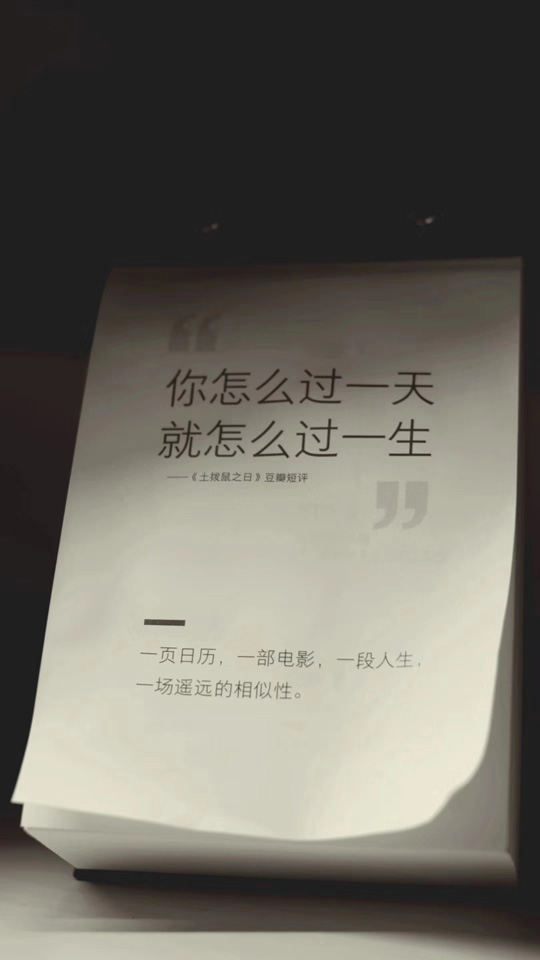1960年我12岁生日那天,父亲送给我一本罗格·彼得森撰写的《北美洲东部鸟类观赏指南》。
父亲酷爱观鸟。我年少时,他就经常向我讲起20世纪20年代他在巴尔的摩的童年故事,讲他如何热爱鸟儿,以至于徒步穿越森林追寻每一种新发现的鸟儿,并为最终能偷偷靠近这些鸟儿观赏一番而感到兴奋。
我还记得,那时我们家就在巴尔的摩西北部绿草地大道旁。12岁生日那天,父亲和我一起坐在家中后院的门廊中,我不高兴地撅着嘴,因为父亲送给我的是他喜欢的“观鸟指南”,而不是我最想要的新棒球手套。那时,我还没有像父亲一样喜欢鸟类和大自然。我心不在焉地翻着父亲送给我的书,直到眼前一亮,被彼得森描绘的一幅靛蓝鹀的作品所震撼。那幅图极其生动,鸟身颜色脱俗,似乎鸟儿就要跳出纸面。
于是,我问父亲:“你见过靛蓝鹀吗?”
“当然,”父亲回答说,“现在咱们这里就有好多。”
他的目光越过家中的草坪,投向小巷对面长满杂草的路边。
“那儿就有一只。”父亲对我说。
“在哪里?”我从书中抬起头来,目光满怀期望地在那片茂密的野花里搜寻着,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
“试试这个吧。”父亲从背后拿出他那架部队配发的双筒望远镜。他之前一直把它放在卧室壁橱的最上层,那里是我不能触碰的禁地。“生日快乐,臭小子!”
他把望远镜递到我的手里,看着我的眼睛。我还记得从他手中接过望远镜放到眼前观看时的情形:鸟儿奇迹般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视野中,这是我年少时见过的最美丽的事物。
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我把这记忆中最美丽的事物也忘记了呢?
父亲就已忘记了几乎所有关于鸟类的事情,大多数时候也忘记了我是他的儿子。他见到我时总是很高兴,不过通常都认为我是他的兄弟或是一位忘了名字的年长的朋友。我要走时,他总是说“没事你应该多来的”,即便我数小时前刚来过。
父亲86岁,属于美国人口中增长最快的群体——超老群。这个群体中约有半数的人患有痴呆症或有不同程度的智力受损,尽管他们的亲属可能不知晓。
每次探望过父亲,如果他还醒着,我会说:“我爱你,爸爸。”当他回答“我也爱你”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惊讶。因为父亲从前绝不会直白地对我说这句话,无论我是他12岁的小儿子还是50多岁的老儿子。现在,我已年近花甲,他也即将90岁高龄,此前束缚他感情表达的严父形象等因素已随他的失忆不复存在,这时,他才能坦然表达对我和弟弟的感情。这可以说是他的渐进性的失智症带给我们的礼物。
身为两个女儿(其中一个正在读研究生)父亲的我今年58岁,父亲在我现在这个年龄时,第一次心脏病发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陆军飞行团服役近5年,幸而保得一命。之后,经营过小生意,但随即放弃。养大了两个儿子,然后重拾对艺术的爱好,创作出几十幅色彩鲜艳的油画。再以后,父亲就开始走下坡路了。65岁获得医疗保险资格的那年,父亲又一次心脏病发作,他的心脏功能从此受损。75岁时,父亲患上了前列腺癌,为此接受了一系列的化疗。81岁那年,他的呼吸变得急促,经常提不上气,随即因充血性心力衰竭住院治疗。
在医院里,他接受了利尿剂和辅助供养治疗。一开始似乎有效,但医院里嘈杂的环境、陌生的面孔、时不时的血液检查,以及往来奔波进行的化疗,这一切让他吃不消。不到两天时间,他就出现偏执和妄想症状,不能吃饭、睡觉,分不清现实和幻想了。越来越严重的精神错乱像狼群般包围着他,侵蚀着他与现实生活的微弱联系——他的家,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儿女。他猛烈攻击这无形的恶魔,尽管攻击的其实是那些带着营养品,想关心、照料他的人。
他时而喊着“离我远点”,时而又清醒似的要周围的人带他回家。他的攻击性越来越强,以至于必须采取措施约束他的行为。先是用药物控制,后来不得不采用外力以避免他伤害到自己和照料他的人。
如影随形的疾病正使父亲变为一个大家不认识、难以接受的人。
自最后一次住院后,父亲已在家住了5年多。他那次出院时,我发誓再不让父亲住院治疗了,原因很简单——我和其他家庭成员都想让父亲待在家里疗养,在他过去27年每夜安睡的自己的房间,直到呼吸停止,身体安歇。我希望届时我能守在他的身边。截至目前,我守住了这个誓言。这多亏了几乎失明的母亲、我弟弟以及一位热诚、尽心的家庭健康保姆的帮助。当然,一定程度上还归功于我从自己也变得衰老这个事实中得到的亲身体验。
有时,我能感觉到父亲现在的思绪和行为背后的那种混乱,能感觉到他在不时抗争,以维持与一个由梦和梦魇交织而成的世界的联系。当往日生活的碎片偶尔飘过时,他因无法理解而变得暴躁、惊恐——
这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真的是我的妻子?我明明记得弗朗西斯是个年轻、貌美,长着一头长长黑发的女人啊。这真是我的家吗?怎么找不到厨房?我记得厨房就在楼下,现在却没有楼梯,我怎样下去做饭呀?这个男人说他是我的儿子,我认识他,甚至可以说喜欢他,但他那么老,怎么可能呢?也许我才是他的儿子,或者是他的兄弟?可我记得我的兄弟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呀——我记得有人告诉过我。我很害怕想到这些问题。为什么我的脸湿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脸湿了……为什么我不能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我到底怎么了?我真的老得这么快吗?我不是刚坐下来吗?怎么就变老了呢?
当他困惑、迷失的头脑试图理解每天出现的这同一组谜题时,我只能站在遥远的彼岸旁观,哭喊。
在另外一些日子,他会对我说:“还记得我们在托马斯灯塔附近捉到的大鲈鱼吗?”于是我们快乐地回忆起那段时光:早晨4点钟就起床,开车驶过童年时那废弃的街道,经环形公路到格伦伯尼,车停在一家名叫“白咖啡壶”的小店,买些培根和鸡蛋,共进早餐,然后把钓鱼工具和5马力的船舷引擎搬到租来的划艇上。划艇停靠在南河边,用力把启动绳一拉,引擎就在隆隆声中转动起来,划艇就开动了。我们闻着引擎排出的浓烈烟气,划艇平稳地驶出河口,朝闪烁着信号灯的灯塔驶去。此时,黎明才在海鸥的叫声和鱼鹰的俯冲中到来。开始钓鱼了,我们敲碎蚌壳,把肉扔到船外的河水中,吸引那些被切萨皮克人叫做“石头”的条纹鲈鱼过来。接着,我们把装了饵的鱼钩抛进撒了鱼饵的河里,等待第一条鲈鱼上钩。父亲记得这一切,然后一下子又忘光了。
以前,他是我的船长;如今,我是他的。现在,他这个当医生的儿子用谈话来填补他那空洞的时间,为他准备每日服用的药丸;在他喘不过气时,为他加服一点利尿剂;在晚上则想方设法减轻他的恐惧——如果某个方法使事情变得更糟,就得立即放弃。作为儿子,虽知道这几乎无望,但仍一次又一次地试图重启他的记忆,梦想有一天,父子俩可以再进行一次灯塔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