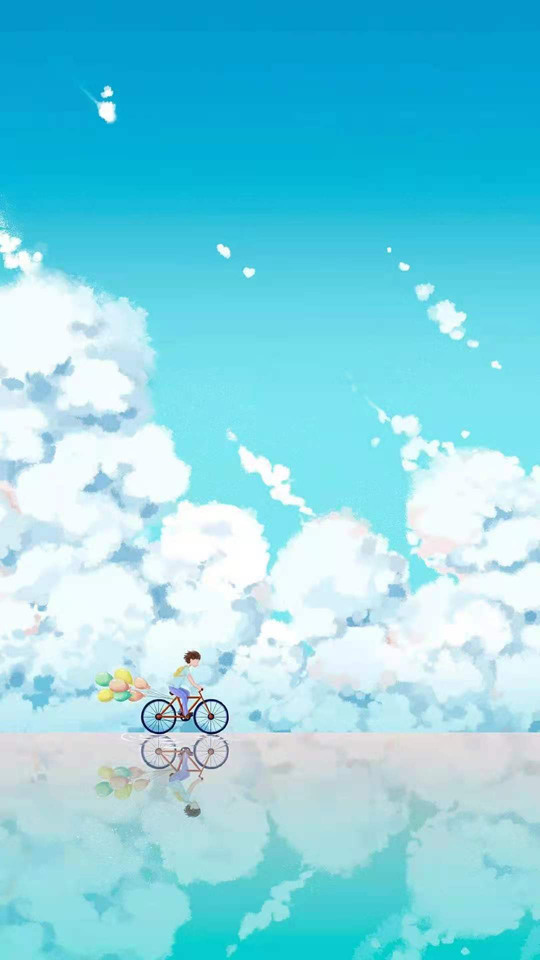十多年前,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为了一份渺茫的爱情,我搭乘“汉中”号客轮,顺江水而下。因为走得匆忙,我未能买到五等舱以上的船票,一张廉价的“散席”,将我抛进生活的最底层。或许是命运就这么安排的,我没有一个坐的地方,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舱,就连爱情也撇下我不管。我知道,这一晚我只能像一个流浪儿,瑟缩在船舱的某个角落,与江风为伴,与寒冷较量,经历一次人生的苦旅。
船儿离港,耳边传来“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的歌声,多么好听,又是多么的凄凉,我的心在漂泊,希望总在远方。独自俯伏在船栏上,回望身后万家灯火,谁知我心中一片迷茫,甚至我苦恋的家乡?
当“汉申”轮驶过南京长江大桥时,华灯初上,大江飞虹,一片辉煌灿烂。在客船的尾部甲板上,一对青年男女兴高采烈地相互以大桥夜景为背景拍照之后,请我为他们拍一张合影,那一刻,我的心忽然为之一颤:在这无边的夜色里,在这漂泊的船上,与所钟爱的人在一起,共享这锦绣时光,不就是一种幸福吗?因此,在我为他们按下快门的瞬间,定格在我心底的,是别人的美丽,我的忧伤。
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我在船上走来走去,仿佛两岸有看不尽的夜景,而事实上,灯火已渐渐稀疏,惟有航标灯在江面上一闪一闪,江涛正高一声低一声,敲打着我的无眠。
夜,渐渐地深了,旅人们在各自或坐或卧的空间,或打盹,或进入沉沉的梦乡。我是散席,没有座位,却到处都可以找到座位。于是,拣一处僻静的地方,铺开一张报纸,我席地而坐,借着昏黄的灯光,翻看着当天的一份晚报,此时,孤独如蚕,心似桑叶。
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有一对五十多岁的农民夫妇,看样子是出门挣钱的民工。他们拿出自家做的馒头干,男人再去找来一搪瓷缸开水,两人席地而坐,吃了点干粮,轮流着喝了些开水,然后,那女人从编织袋里拖出一条旧棉被,利索地一抖,盖在两人身上。他们说了一会儿话,就像在自家简陋的农舍里,那男人甚至还轻轻地为女人掖了掖被角,然后,在这涛声依旧的客船上,朝着赚钱的方向,打起了美妙的呼噜。
半夜时分,我被冻醒了,早春的江风,直往船舱的缝隙里钻,而我只盖着一张薄薄的报纸,冷,是实实在在的。于是,我索性走出船舱,活动活动身子,再去看看江上的夜景:下弦的半个冷月,悬在这九天之上,脚下是万顷波涛,向东滔滔奔流。茫茫夜色里,我感到一种虚空,一种无边的茫然。客船偶尔拉响汽笛,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仿佛是一种呼唤。当我再回到船舱,看到我的“一纸薄被”已被风吹离原地老远。那对农民夫妇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醒来,只见那男人把被子一横,对我说:“小伙子,船上夜凉,外面风大,如果你不嫌弃,就将就着和我们合盖一被,过一会儿,天也就亮了”,那女人看了看我,接过去说:“其实,我儿子和你也差不多大,他在南京读大学。”我只觉得心头涩涩的,又暖暖的,一种难以言状的滋味堵着我的胸口。是的,我是农民的儿子,还有什么可说呢?
其实,人生旅途上,我们毋需太多,“良田万顷不过一日三餐,大厦万间只要身眠七尺。”有时候,我们总是在别处寻找爱情,寻找幸福,而爱的真谛,幸福的源泉,时常就在我们身边,它也许很寻常,很朴素,譬如今夜对我来说,爱情就是那在大桥下留影的一对青年,和我身边相挽相扶、磕磕绊绊走过半个多世纪风雨的农民夫妇,而幸福就是一床哪怕洗得发白的被子里的老棉,它会温暖着我,也温暖着天下所有孤单的人,平常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