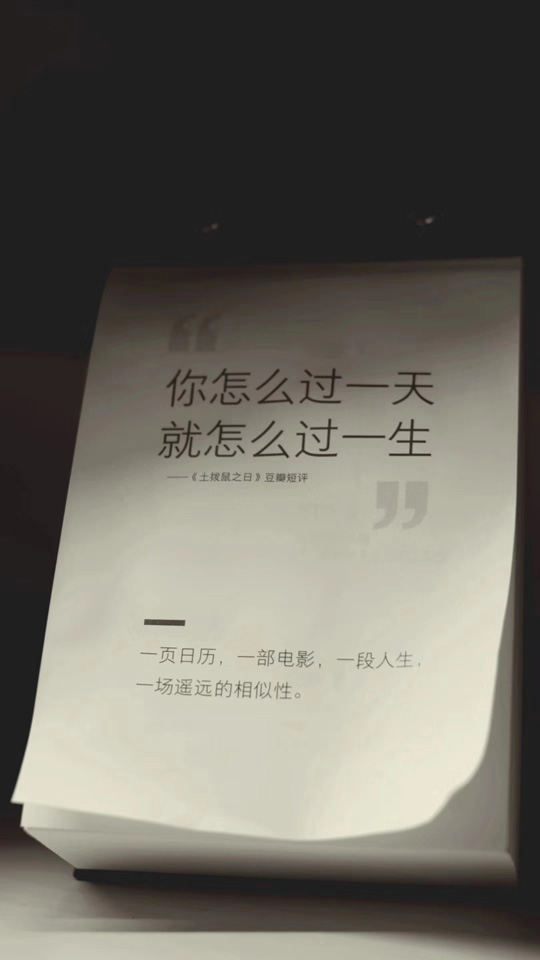记得在我快复员的前夕,我娘到北京看我。没想到突然发病住进了北京军区某医院,一住就是八个月。我隔三岔五去看望,那时我笨手笨脚的,常常把袜子和裤衩一块洗。伺候我娘的差事全由一个秀气的女老师负责,她母亲因为心脏病住院,就挨着我娘。我娘生了五个小子,就是没有闺女,见了她总喊她闺女。女老师就照我的称呼,跟我母亲喊娘,声调特别亲切。我在家行五,日子久了,女老师就喊我老五。我觉得不见女老师心里就空落落的,许是初恋缘故,我很少单独和她在一起,那种耳热心跳的感觉现在回忆起来好像在昨天。女老师对我倒很大方,当着她母亲和我娘的面总爱和我聊天,那双眼睛常常盯着我喘不过气。
我和她的交往就是借书和还书,然后谈读后感。两人谈到一起时,又总是激动不已。我娘和她母亲在一边总是笑,笑我们发痴。当我们朦朦胧胧的时候,我娘早看出我们之间那点意思,但就是迟迟不表态。
有一次,女老师对我娘开玩笑地说,把你家老五留在北京吧,北京有发展。我娘对我这个老儿子视为宝贝,哪儿舍得放我,警惕地说,不行,他不能离开我。女老师笑了,他那么大人了,还离不开您哪行啊。我娘不再说话,女老师也不再问。
娘病愈出院前,女老师找我,两个人在医院的花园里来回走。那时不懂得说什么甜蜜的话,明明知道手拉着手就是一种幸福,但也都是故意装得很正经,谁都不会去触动谁。我说,我准备复员回天津。女老师忽然哭了,说,我母亲有病,我不能离开她。我对你母亲这么好,你就不能跟你母亲说说,把你留给我?
我跟娘摊牌,帮助我娘回忆在她住院的日子,女老师怎么伺候她的,女老师为我娘洗脚,甚至擦身上。有时,我娘尿尿不方便还给接尿。我娘爱吃西红柿,那时已经入冬了,买不到西红柿。女老师跑到郊区,找到大棚里,拎出一兜发青的西红柿。菜农说,别马上吃,要在温水里泡泡。女老师就回家,在洗脸盆里倒上温水,把西红柿泡上。她这人痴心,时不时用手去试温度,只要凉一点儿就立马续上热水,三个小时没有停闲过。然后,捧着软软的西红柿送给我娘,把皮剥净,递给我娘。我娘背后要起褥疮,大夫说得经常按摩。又是女老师,天天给我娘按摩后背,直到大夫说行了。我对我娘说,就这样人家怎么就没感动您呢。我娘说,我喜欢她,但我不喜欢她母亲,你跟了她,就得受她母亲的委屈,你行吗?
我最终还是依了我娘,没有和女老师继续发展。我复员离开北京时给她家打了个电话,我对她说要复员了,后天就走。女老师说,你想见我?我说,是。女老师沉了沉说,还有什么意思吗?我羞愧地说,你不想见就算了。女老师说,来吧。她家在北太平庄住,那是一个深冬的夜晚,我到她家时,她在楼外面正等我。女老师说,别上我家了,我母亲见了你也别扭,咱俩走走吧。
于是我们步行,从她家一直走到西单,足有十几里地。天特别冷,她穿着棉猴儿,只露着两只眼睛,就这眼睛烫得我脸颊通红。不能再送了,天太晚了,马路上空荡荡的。女老师拉着我的手,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也是最后一次。她说,分手了就不要再联系了,彼此留个感情空间吧。我嗓子眼发酸,什么话也没有。很想拥抱她,但不敢。估计她也想,眼巴巴看着我。两个人憋了一会,我把她的手松开,她失望地对我说,你是我的初恋。说着她泪如雨下,转身上了最后一辆公共汽车。此后,我就再也没看到过她。
后来,偶然的机会,我在护国寺的胡同口遇到她妹妹,便上前询问她姐姐的情况。她妹妹说,我姐姐结婚了,生活得不好,但你也别再打搅她了。又过了几年,我出差去北京便跑到北太平庄,四处寻找她的家。但灰色的旧楼已经没有了,全是清一色的高层住宅。我又跑到她所在的学校,校舍已经没了,变成一个超级大商场。过去熟悉的一切都没了,都消失了。女老师在哪呢?她现在是不是好些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