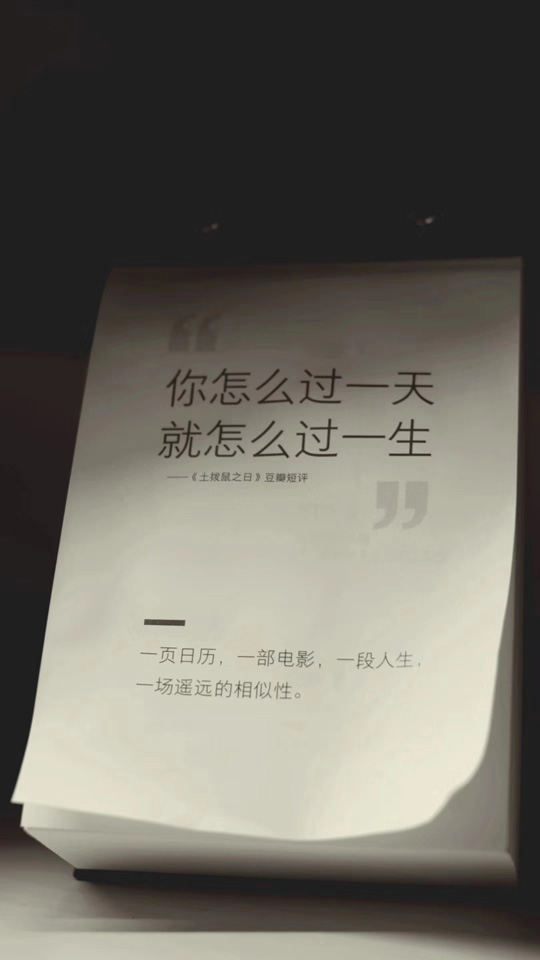1
她的名字叫意婕。
她第一次出现在他眼前,只有五岁,穿着短裙,浑圆粉藕似的手臂上,套着一只鲜红的、晶莹的玛瑙鐲子,稀疏柔软的发丝束在头顶,系着一条天蓝色的发带。微风吹过,裙上的荷叶边儿飘飘的,灿亮的发带飘飘的。她的小手握在她母亲手中,她母亲正和他母亲说话:“你们能搬来真是太好了!这地方环境不错,就是偏僻了点,我们咪咪最可怜,连个玩伴也没有,附近都是野孩子!咪咪!去!跟小哥哥玩!”意婕被她母亲推到他身边,他下意识地退后一步,她母亲开怀地笑起来:“小男生还怕羞啊?你们儿子真乖,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
“哲生!”他母亲有些愠怒,拍着他的背脊:“带咪咪去玩儿啊!你弹钢琴给咪咪听!”
两个小孩儿坐上钢琴椅,哲生有板有眼地弹完“河畔明月”、“平安夜”,意婕的眼睛又圆又亮,眨呀眨的,小巧的嘴唇忘情地启着,他的双手平放在琴键上,转头看她:“好不好听?”
意婕用力点头,她的童音又甜又软:“好棒哦!小哥哥!你好棒!”他微笑着,牵起她的食指,轻轻敲在琴键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意婕小小的身子一震,又紧张又兴奋,她扬声笑起来,双眼更晶亮了。他也笑,握着她的手指云敲其他的琴键,一连串杂乱刺耳的声响此起彼落,她又叫又笑,他满心都被奇异的兴奋胀满了,于是,他也一直地、歇斯底里地大笑。
她很快地与他熟悉起来,他牵着她的手上学、放学,假日里,两家大人正好凑一桌麻将,他带她爬山、上树、捉蝌蚪。天晴的时候,他们爬到树上,可以看见家,看见爸爸办公的大园子,还有学校的操场,追逐奔跑的小朋友。下雨的时候,他采下野山芋的大圆叶,做成一把绿色的大伞,两个人躲在伞下,还是湿淋淋的。“你不要叫我咪咪嘛!”她常有些小小的抗议:“好像小猫咪的名字一样!”
他后来再没有叫过她“咪咪”,一直都叫她“意婕”。她说的话,他全放在心上。他宠她、纵容她,原先有些孤僻的性格,也为了适应她,渐渐改变了。
有一回,他也对她生了一次气,只因为她对人说哲生是她哥哥。
“谁是你哥哥呀?”他满心不高兴,也说不上是为什么,就是那样犯别扭。
“好嘛!好嘛!不要生气了,小哥哥……”她走在荷花池的边缘,低声求饶。
“叫你不要再叫我哥哥了――。”他第一次对她吼叫。她一惊愕,“扑咚”一声滑进池塘。
不过是转瞬间的事,哲生用力抓住她,然而她的半截身子陷进了泥塘,他抓住她的手,却抓不住她继续下陷的身子,她喊叫挣动,陷得愈书。
“小哥哥――”她惊恐地望着他,怎么也脱不出这个可怕的泥坑。
“不要怕!”他的声音凄厉地:“我拉你!拉你出来――”
哲生拼命拽住她,他是个细瘦的九岁男孩。拗不过整个神秘的黑窟,拉着扯着,他开始哭起来。
“小哥哥!我好怕!有人拉住我的脚啦!”意婕微弱而费力地嚷叫。他拉不动她,也无法向人求援,他知道自己一旦放心,她就会被整个泥塘吞没了。“真的,有……有人拉我的脚啦……”意婕再度呻吟。他再也无法按捺心中的恐惧与愤怒,声嘶力间竭,乱七八糟地狂喊:“走开!走――走开!不要拉她!不要拉她!放开她!放开她――。”
他恐惧她将离开他;愤怒有人将她抢走――他只有拼命,拼命地拉着他的意婕……她的身子活动了,多么神奇!他渐渐拖出她了,她在他的协助下,爬出池塘,瘫软地坐在草地上,除了雪白的小脸,浑身都是污泥,她低头从足踝上解下一段水草,对他说:“这个……拉我的脚……”
说着,眼圈一红,掉下泪来,由哽咽变为嚎啕,他也跟着哭泣。
他带着她找到一个水龙头,冲去身上的污泥,俩人坐在午后的阳光下,晒晒湿衣服。树上的鸟鸣聒噪,知了正卖力地嘶喊,卖枝仔冰和冰淇淋的小贩来了又去,他们只是坐着,没有说话,像在刚才的一霎间,成长了许多,不只是个六岁和九岁的小孩了。她的鞋子,在方才的一场“劫难”中遗失了,要回家的时候,他替她脱下仅存的那只鞋,对她说:“我背你回去!”
他背着她,提着她的鞋,往回家的路上走,那片荷花池塘在夕阳下分外美丽,却令他的心一阵阵惊悸。能够感受到意婕的心跳与呼吸,是多么美好,倘若……他想着,心底一阵酸楚,纷纷地落下泪来。
她回家后还是生了场病,差点转成肺炎。大人们事后也追问发生了什么事,她轻描谈写地说:“我掉到池塘里面,哲生救我真起来的……”那次以后,她再也不叫他“哥哥”了。“喝了水没有啊?”大人问。
意婕摇摇头,她父亲一把抱住她,宠爱地:“好啊!虾蟆不吃水,太平年――”
一屋子的人都笑起来,她带笑的眼眸在他脸上一闪,垂下头去。他的心紧紧一缩,缓缓舒开来,第一次切切感动,因她是个女孩。
2
上了中学,他们仍是形影相随。他高一,她初一,放学之后,在一起做功课,他的母亲最擅长烘焙小点心,他们边吃边谈,直到她母亲在隔壁唤她回家吃晚饭。
他一直没有放弃钢琴,并且自己练习谱曲,把他们共同喜爱的诗词谱成曲。初三那年,她抄了一首李白的诗,送给他,那是李白的长干行: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
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
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
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远道,直至长风沙。
他拿着那首诗,心头一阵酸涩,一阵激动,她那年正是十四岁呵!天!多好的一首诗。
他在当天夜里谱成了曲,重新抄写一遍,投进她家信箱。那天晚上,事情爆发了。
意婕被她母亲拖着冲进他家,他父亲不在,他母亲连忙迎出来,他开了大门,直视着她苍白的脸,她垂着头,短发零乱地披在脸上。她母亲朝他母亲咆哮起来:“你们家的人太厉害了!你先生会做人,是主任面前的红人,凭什么欺负我们?哦!好事轮不到我们,却要调我们到那么远的鬼地方去?是什么意思?”
“事情不是这样的,你们要调走,我们也难过……”他母亲低声分辩。
“少来这一套了?冯太太――别在这儿猫哭耗子假慈悲!今天大家把话说清楚,我们哪里得罪你们?逼得你们借刀杀人――?”
“这是什么话?”他母亲转向他:“哲生!带咪咪到你房里去……”
“干什么?干什么?”她母亲一下子暴跳起来。
“原来是你这个做娘的教唆你的儿子勾引我的女作啊!当着我的面,你也敢――?”
他母亲的脸一下子沉下来,当她生气的时候,总是格外冷静:“楚太太!我实在无法想象,你会说出这种可怕的话!你侮辱的不是我和我儿子,还有你一手调养的女儿。”
意婕抖瑟地,张开嘴,发不出一点声音。她母亲扬起手中的纸张,走向他的母亲:“我的女儿我管教不严,你的儿子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东西……你看看!这算什么?”
他母亲接过那张纸,好容易将冰冷愤怒的目光从纸上移开,望向他,清清楚楚地问:“哲生!这是怎么回事?”
他心中十分明白,明白母亲所要的答案,他只要说出事实,他没有“勾引”她,这是她送给他的……他的眼光转向意婕,他已算不清这是今晚第几次的凝望,但,她总不看他,总不抬头,窄小的肩膀抽搐着,不知是哭泣?或是恐惧?那份无助的凄楚,令他想起陷在荷塘中的她,挣扎而不断沉落……
“是我!”他猛地一喝,三个人都吓了一跳,意婕终于抬头看他了,她眼眶蓄泪,对他摇头。但,她已不可能阻止他了,他说:“是我送给她的!因为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喜欢这首诗,以为她也会喜欢,所以,就送给她了!我们并没有别的意思,为什么……?”
“够了!”他母亲阻止他说下去:“明年夏天就要考大学的人,哪里还有这个闲工夫?真是不像话!”
她母亲撇嘴笑了笑,酸溜溜地:“反正我们就要搬走了!我只是要跟你们讲明白,我的咪咪可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女孩,以前是小孩子,在一起玩玩也就罢了。现在半大不小的时候,我可不希望哲生再来找她,万一……。”
“你放心!不会有万一,我的儿子我知道――。”
他凄惶地注视她,她也正盯着他,默默地,像在点头,又像摇头,咬紧了下唇。
她或许是放弃了,上学或放学,总要找个同学作伴。他绝不肯放弃,就为了那首诗,就为了父母之间的恩怨纠葛,将一切都毁灭,让一切都烟消云散,他不甘心!她怎么能甘心呢?
他终于找到机会,那天放学,她终于一个人了,他一直跟在她后面,直到远离所有的人群,他走近她,低声呼唤:“意婕。”
她握着书包的手臂缩紧了,脚步也加速了。他跟上去,再一次唤她:“意婕。”
她拔足而奔,他跑得更快,一下子拦住她。她停下来,微喘地瞅着他,他深呼吸,也盯着她看。他们对望了一阵,她把眼光调开,望向天空。他下意识地随她仰望天空,秋天的蓝空中,澄净的一片云也没有。当他收回目光,才发现她哭了。
“不要哭……”他心慌的,鼻子也酸起来:“我知道你妈妈不准我跟你说话,也不准你理我!可是我们没做错事啊!为什么要让他们影响我们呢?”
她把小手绢拧成一团,擦拭滚落的泪珠。
“记不记得小时候,我们多快乐?我现在宁愿自己还是个孩子,长大了为什么这么烦恼呢?”他问她,也是问自己。她不说话,好容易抬起头,向点点头,唇边似有一个隐隐的笑意。他松了一口气,微笑地问她:“我们恢复邦交了?”
她点点头,他开心地笑起来:“我们明天――老地方见?”
她悄悄一颤,望着他,迟疑地点点头。他张开嘴,忍不住想欢呼,向上一跃,他说:“你先回去吧!免得让你妈看见……”
她点头,向前走了几步,忽然回头看他,他站在原地,双手叉在裤袋中,向她说:“明天见!”
她勉强现出微笑,困难地说:“再见。”
一转身,她掩面飞奔而去,他诧异地跟了两步,她哭泣着跑远了,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悲伤地哭泣?
第二天,放学之后,走过她家,矮墙内的花草树木有些零乱,他伫立在那儿,蓦地有些神经紧张,一阵风过,吹开了大门,他奔跑过去,穿过她家小小的庭院,站在一片空旷的客厅中,她搬走了!无声无息地走了!
一切都是静止的,如一场梦魇……他家烘焙点心的香味,融融地飘浮在空气中……
3
他如愿考上音乐系,离家去过住校生活,这是一个转折点,从群体生活中感受到乐趣,学习调适自己的人际关系。大学以前的生活逐渐淡去,像云烟。然而,总有一丝薄云,柔柔地、软软地、淡淡地缠绕在心头……那个小女孩,他再没有见过她,听过她的消息,有时候,连她的面貌也模糊了。只有初见的浑圆可爱始终明晰,最后一次见面,她只对他说“再见”……一个自童年开始的朋友,到底是份怎么样的感觉?他也迷惑。刚升上大四那年秋天,餐桌上,他父亲不经意地告诉他们,她的父亲肝癌过世了。他一惊,搁下碗筷,浮起她父亲那双爱笑的眼睛,拥着意婕唱:“虾蟆不吃水,太平年……”
他悄悄找到他父亲的同事高伯伯,带他到公祭的灵堂。站在灵堂外,望着披麻带孝委顿灵前的意婕,他感觉像隔了一个世纪的久远。看不见她的脸,只见她一次又一次地叩头答礼,这女孩就是意婕吗?他远远地望向她。
高伯伯先走了,他仍站着,等着人们将她父亲的灵柩抬去火化,等着人们扶起意婕,将灵位和一些其他的东西交给她捧着,她几乎站不住,却勉强地迈着步子,低垂着头,和,向外走来了。他紧张得听见自己的心脏狂跳,盯着她走向他,终于,终于到他面前了!神奇的,她突然抬起头,望向他――一瞬间,这张面孔,所有的记忆,全部鲜活起来。她瘦了,圆脸成了尖脸,眼睛更大了,盛满哀伤与沉静。他张大嘴,几乎就要喊出她的名字,但,她似乎是视而不见地收回视线,再度垂下头。他怔了,费力地闭上嘴,不能置信地望着她被人拥簇而去的背影。怎么可能?她不认得他了?她没理由认不出他的,如果她是意婕!为了来见她,他费尽心机,他放下即将来临的期中考试!他变了吗?他迫切地找寻一面镜子,直到找着一片可见人影的玻璃,他看见自己,没有改变啊!他始终是这样的。可怜的意婕,小时候,有什么委屈她总是对他说的。而现在,她竟然不认得他了!强烈的不甘包围住他,在浓浓的秋天里,他渐渐明白了,这是一切怎样的情感。二十九岁,他从欧洲回国,带着创新的中国音乐,在乐坛上掀起震撼。他将诗词合乐,用现代人的眼光诠释,带起歌坛“寻根”的热潮。
这年春天,他忙坏了,周旋在音乐会、唱片界及各种新闻媒体中。直到医生警告他:情绪紧张将影响他的肠胃时,他决定暂时离开人群,给自己一段休闲的日子。
他“隐居”在淡水,一位教授的家中。看淡水河的日落;看渡船;看海上的日出;看淡水站上火车的去来。他喜欢坐在充满人声笑语的地方,毫不戒备地放松自己,有时候感觉自己像个游魂;而且是个高大的游魂,走来走去,都不引人注意。他真喜欢这种淡淡的日子,什么都不必思考,自然就有些新鲜的东西涌进心灵,塞得满满的。那天,不由自主地逛进一家唱片行,唱机正声嘶力竭的吼着时下最流行的翻译歌曲,他本来已经走过去了,却没什么道理地又走回来。唱片行有个年轻女子背对着他,正向站在高处的老板喊叫:“是新出的唱片,不是旧的!”
因为音响声太大,老板也必须扯着嗓子。
“没有啊!是唱的?还是音乐?”“是音乐。”那女子费力地嚷:“我昨天还看见的!冯哲生的‘梦回古中国’专集……”
她说着抬手指向唱片柜,一只鲜红晶莹的玛瑙手鐲子闪在他眼前,他猛地一窒,冒了一身汗――不会!不会是她!怎么可能,那截手臂细瘦得仿佛不经意就要折断了……那女子颓丧地转过身,他们面对面地凝望。她所有的表情在一瞬间凝在脸上,而他,拼命稳住自己的呼吸心跳,凝视着这个一眼就能认出的女孩,久久的,才从喉头深处流泻出那声呼唤:“意婕。”
“怎么……”她像梦呓般呢喃:“怎么可能?”她的神情始终像在梦幻中,当他们走在石板道上,海风掀翻她的裙摆和宽袖,恣意地将长发散在她面颊上,他终于忍不住问:“好吗?”“嗯?”她的双眼迷迷蒙蒙,忙着扯裙角,理长发,慌乱而不自然地:“还好。”
他点头,竟想不出什么话,好容易开口,竟是两个人一道说:“你……”
俩人一道煞住,笑起来。
“你先说吧。”他含笑让她。
“我是说……常在收音机里,听见播你作的曲子,实在很好听哪!”她说话的时候不看他,好像他根本不在她身边似的,他不禁揣想,她或许常是这样对他说话,只是,他一直没能听见。
“你喜欢,我可以送你两张唱片。”
“不用了!”她急切地:“不用!谢谢!我自己可以买……”他微愕,有些不对劲,却说不上是哪儿,他谨慎地闭上嘴。又走了一段沉默的路,他小心翼翼地问:“你现在在哪儿做事?”
“我在这里一家小公司当会计……”她讪讪地笑着:“也没什么大出息――”
“别这么说。”他急忙打断她的话:“行行出状元!”
他们在海边坐下,他问:“什么时候搬到淡水来的?”
“那年,我爸爸去世了,妈就带我到淡水来了。这儿是她的娘家。”
“哦。你在哪儿念的大学?”
“大学?”这两个字像蝎子,突然螫疼了她,她的脸上仍挂着笑,眼中却流露一股陌生的冷冽:“大学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念的!我当年也想!想得快要疯了,可是……”她凄怆地摇头:“算了!我没有这个命!”“为什么不来找我?”他一下子问出口,要收,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定会帮助你的……”
她睁大了眼睛看他,眼中渐渐浮起温馨的光彩。那些甜蜜的回忆,同时轻叩她的心房了。
“那年,伯父公祭,我去了……”他娓娓诉说:“看见你,我一直守在外面,可是你……”他踌躇了一会儿,说:“你没看见我!”
她突地仰头望天,这个动作,是他熟悉的。他密切注意,怕她掉下泪来,她没有落泪,只是晶亮了双眼,有些颤声:“我看见你了!可是,我不敢相信,我以为……是幻觉!不可能是你……我那时候感觉自己快死了,跟爸爸一起死了,我以为,人死以前,都会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人……”她停住,用手捂住脸:“我搞不清……怎么回事。”她的玛瑙鐲子,又露出来,她幼年时戴的,现在竟然还戴着,可见手臂有多细瘦,不仅是手臂,她全身都纤瘦。他的心,凄凄恻恻作痛:“你没有好好照顾自己,这么瘦……”
她一凛,抬头看他,脸上的感动和迷惘迅速退云,她挺直背脊说:“要结婚的人,没有不瘦的。”
他盯着她,思绪全被抽空了。茫茫然地问:“谁结婚?”
“我啊!”她看着他,紧张地握住裙摆。“你……?”他傻傻地笑起来:“你要结婚?”
“很好笑吗?”她问,有些咄咄逼人。
“不!不是!”他连忙收敛,却管不住牵动的嘴角:“是意外!那年,见到你,你才这么一点大……”他手忙脚乱地比画。
“胖嘟嘟的,扎一个蝴蝶结,最爱弹我的钢琴……”他的手停在半空中,望着面无表情的她:“你忘了?”
“没有。那年我还不到六岁,现在已经二十六了……”
“是啊!”他迷乱地接口:“时间过得真快!叫人……”
叫人不敢相信的,又岂只是飞快的时间呢?
“你呢?”她问:“应该有很好的对象了吧?不要为事业耽误了终身大事啊!”“我不行!”他再度笑起来,笑得疲惫,“我流浪惯了,根本定不下来――。”
他说着看她,她正咬住下唇,默默看着他,像是点头,又像摇头。一股暖意自心底泛开来,他觉得她依然是懂得他的。
“我明天晚上结婚,所以今天才能有自己的时间出来逛逛。”她对他说。他无法接腔,她在结婚前一天,逛进唱片行,买他的唱片。而他偏也走进那家唱片行,在同样的时刻里……世上许多事,原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他渐渐明白。
“明天晚上,你能来吗?”她问。眼中有些闪烁的东西,分不清是期盼,还是担忧?曾经,她是颗星子,浑身都发亮;如今,她是个娇弱的淡水新娘,夕阳为她镀上一层层柔和的金黄。她在他眼中是熟悉的,又遥远而模糊,荡荡漾漾……。她见他不回答,自顾地笑起来:“其实,俩人结婚,也没什么好看。你现在是名人,一定抽不出时间……”“真的,太不巧了……”他说,带着歉意的微笑。
“我今天晚上就回台北了。”这是两秒钟前作的决定,而无改变的余地了。
“那……好吧!”她站起身,长发和裙摆又在风中狂舞起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了……”她说着,望向他,他的眼光掠过她,投注在海面上,耸了耸肩,轻劝笑起来。
“在这儿遇到你,是最大的收获!真的。”他们像一对普通的朋友,握手告别,然后,各奔前程。有一些东西结束了,有一些正在开始……
他到淡水来,本就是有些许期待的。孤独的背起行囊,当天夜里走向淡水车站的时候,他仿佛寻到答案了――长干行,无论怎样绮丽、动人,毕竟只是古老湮没了的故事。只能合乐……
她最后一次出现他眼前,削瘦地挺立在海边,她用两只手压住裙摆,按住长发,无法向他挥别,只凝视着他,点头又摇头。海风太强,他几乎站不稳身子,她去稳稳地伫立,仿佛她一直就生长在这里的,一个完全成长的女子。
她的名字叫意婕。
她仍是他二十几年回忆中唯一的温柔。